【青海记忆】儿时的美食记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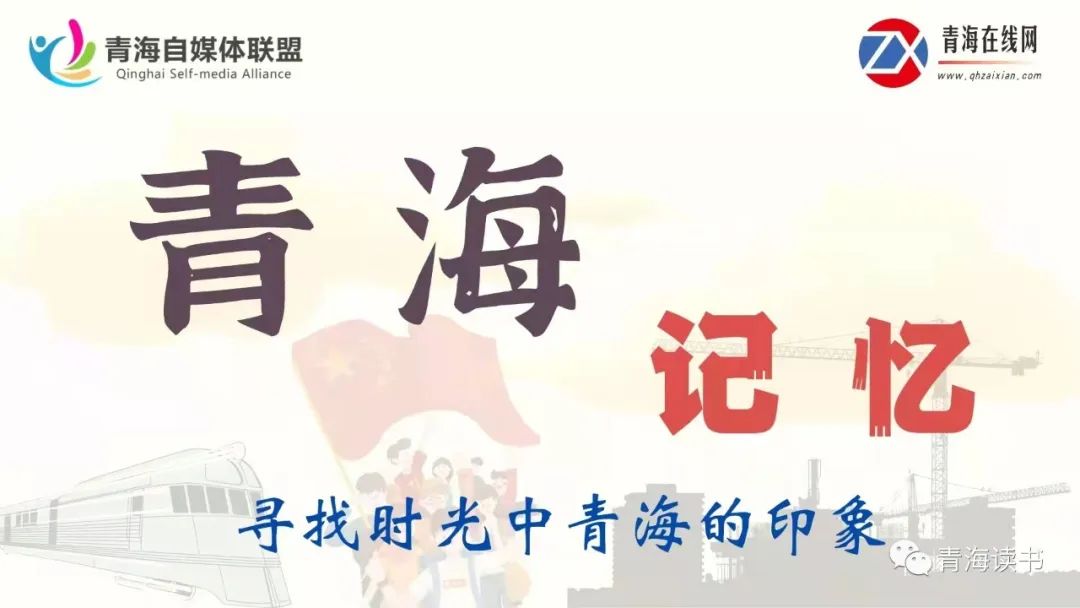

每当过年,品尝着年三十晚上丰盛的年夜饭,或走亲访友时看着满桌子的美食,我就不自觉想起小时候美食单一,但年味很浓,人情很稠的那个难忘的岁月。
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度过的。那时候,正值文革或文革刚结束,农村还是大集体时代,吃饭靠挣工分,大部分地区很贫穷,有的地方刚刚对付温饱,有的还连温饱没有解决。过年过节当然不可能吃食很丰盛。过年杀一头猪,能吃上肉已经是很不错的好日子了。
当时,农村乞讨的特殊现象还没有根绝。我也没有想明白,不知道为什么解放多年了,但还有那么多的乞讨大军时常光临村庄。记忆当中,这些乞讨大军人数可谓不少。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,有四十不惑的妇女,也有半大小孩……看上去让人心酸心疼。但不论谁上门乞讨,趁过年谁家都会大方地施舍两个花卷馍馍,或者油饼馃子大麻花。若碰上头发花白,步履蹒跚的老者,或者蓬头垢面可怜兮兮的小孩,还会舀给一碗我们当地人过年吃的烩菜。烩菜汤汤水水,有荤有素,有肉有菜,让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吃上一顿热乎饭,算是寒冬里和我们一块过了个温暖年。“对乞讨的人不能无礼,尤其过年的时候更要持之以礼……”大人交代的事,教我们小孩子做人的话,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
让人记忆深刻的是,那时候市场上物资匮乏,很多日用品还定量、限购。比如,扯布要购布证,买肉要副食品供应证,下馆子吃饭除交钱外还要交粮票。那时,饭馆不叫饭馆,叫国营饭店,或国营食堂。粮票有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两种。在我有限的记忆里,除过过年,儿时吃到肉见到荤腥的就有那么一两次。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,七八十年代到国营饭店“奢侈”地下过两次“馆子”。

一次是父亲上街办事,办完事带我去吃的水饺,我记得国营饭店那个水饺,白白胖胖的,大珍珠一般,玲珑剔透,可爱极了,不忍下口。和家里包的饺子比起来,它形小精致,没一个褶子,胖墩墩的,倒真正像一个金元宝。想到金元宝,我赶紧用筷子搛起来一个,放到嘴里,一口吞下,吃下去的那个滋味,真是没法用言语形容。父亲边欣赏饺子,边咂摸饺子的滋味,边和周围下馆子的人喧起干单来。
“这饺子咋这么精致?”父亲念过私塾,他把饺子的娇小说成了高雅的精致。
“机器包的。肯定是。”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农村装束的人回了这么一句话。
“机器包的?机器还会包饺子?”父亲不相信似的在惊叹之中又反问一句。
“手工是端端包不出来。你看一样的大小,一样的形状,一样的圆鼓鼓,不差分毫……”那人言语中像见过世面的样子,让人不得不信服和赞同。
大概一碗饺子不贵,来店里吃饭的人很多,大多是头戴草帽,穿布衣,敞开怀吃饭的人。
此时,我感觉我们的镇子就像鲁迅笔下安逸的鲁镇。嘈杂的市井,叫卖的贩子,跑堂的伙计,来来往往肩扛农具的农民……饥馑年代少有的和平景象。
父亲虽然读过私塾,但书本以外的不甚了了。听店里人言语,父亲不再说什么了。独自欣赏起机器包的饺子来,就好像在认真欣赏一件哪个大师的艺术品。我不知道包饺子手工和机器有什么区别。我看父亲的神态似乎信以为真了。可能父亲和那些人想法一样,吃上了一顿机器包的饺子,从此就成了见过世面的人了。
机器包的饺子,玄乎又玄乎的事情,那时闻所未闻,在农村人有限的认识中,不仅当做了不可思议,而且以为那是一件稀罕事和奇事。不管大人们怎么想,吃了机器包的饺子,我心里是乐滋滋的。回村去也有了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:“哈哈,国营饭店机器包的饺子就是香啊……”好像下了一次馆子,我也经历了一次大世面,身份也不一样了似的。国营饭店的饺子和家里的一碗三四个大饺子确实不一样,玲珑剔透的“珍珠”让我感到吃惊的同时,小小的年纪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第二次是1982年和几个同学到县城的国营饭店嘬了一顿臊子面,那味道确实香极了。至今再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臊子面。可能平时少油无肉,一顿见荤的臊子面,把我的记忆定格在了那一瞬间。感觉天下再美的美食也抵不过那一碗臊子面。其实,国营饭店或者食堂就是一个平房瓦房,和八九十年代路边的普通饭馆差不多,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国营饭店就是一栋现在的大酒楼。那时,我初中即将毕业,我们五个同学凑钱到县城国营饭店吃饭,我的一个同学脑子灵活,在买饭口交了钱和粮票,在取饭口取饭时多取了两碗,愣是没被懒洋洋的公家人——服务员发现,我吃完后看着沾了便宜的另两位同学狼吞虎咽第二碗臊子面,觉得刚才的一碗只是塞了个牙缝,苦于没钱只好吞咽自己的口水……
几辈子,农村穷农业苦农民难,谁家都一样,平时基本上见不到肉星,除非到了过年的时候生活才得一改善。八十年代以后,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实行农业大包干,农村很快甩掉了贫穷落后和吃不饱饭的贫困状况。2000年,实施退耕还林政策,农民不种地还能领到生态补贴。2006年,国家又取消农业税,还给种地大户发放种粮补贴,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,农业经济和农村生活进入快速发展和改善的好时期。收入增加了,住房首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大瓦房多了,楼房多了,土坯房不见了……人们对进步、时尚和幸福生活的追求,也体现在过年的仪式感和对小康生活的体现上。“烹羊宰牛且为乐,会须一饮三百杯”,你看,到了腊月,家家户户要做很多好吃的,年夜饭和过年少不了美味饺子和鸡鸭鱼肉,人们讲究敬天祭祖,讲究感恩美好生活,讲究吉祥安康,年年有余……这不是攀比,也不是浪费,更不是招摇,农人们勤俭持家惯了,但心里有一杆秤,他们图的就是一个过年时的团团圆圆、心气顺畅和精神快乐。
生活,不就是灯火可亲和家的温馨团圆嘛!
祁万红,六十年代生人,是曾经工作在牧区的一名河湟人,退休后以读书写字健身为日常。自己的格言是:无意多大建树,只要心满意足就好。青海读书会签约作者。

